嘉宾简介:
杨雄里,神经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现任复旦大学教授,脑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大辞海”“辞海”副总主编。长期从事神经科学研究,关注视网膜信息处理机制及相关临床问题的基础研究。
张嘉漪,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脑功能与脑疾病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拥有交叉学科背景优势,围绕视觉功能的修复和编解码主题开展研究。

划重点:
1.对于失明者的治疗来说,恢复光感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对图像的辨别,为了达到这一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人工智能按照自己的发展态势,很可能创造出一种新的智能方式,在解析复杂的问题时,不一定比人脑在进化过程中所塑造的智能更差。
3.在脑机接口的应用过程中,工程上的难题会有,但总能解决,倒是涉及伦理问题更具挑战性。
4.美国削减经费带来较大规模的科学家流动,这可能会改变国家之间的科研实力现状。
出品|搜狐科技
作者|周锦童
编辑|杨锦
杨雄里记得,小时候看丰子恺先生的漫画童话故事,想象在某处有个特殊的民族,每个人的腹部都是透明的,脑子里想什么,旁人就可以从那个人透明的腹部看到。当时他就想:“如果确是这样,哪里还有个人隐私可言?更谈不上保护个人的隐私了!”
实验已证明,一个人的脑电可以影响另一个人的活动,假设有一天所有脑电波都可能被解密,又没有严格的规则、制度加以管控,那人类社会将成何体统?
作为资深的神经生物学家和中国脑科学计划的倡议人与推动者之一,杨雄里一方面欣慰于人类科学前沿的突破,另一方面对将来可能出现的所谓“脑控”的滥用感到忧心忡忡。
放眼全球,科技狂人马斯克让脑机接口极其吸引人的眼球,就在前几日Neuralink公布的2025年夏季进展中,不仅展示了七位植入者用意念操控游戏、机械臂的突破性成果,更勾画了2026年实现盲人视觉重建、2028年完成全人类与AI互联的蓝图。而在国内,脑机接口同样正在驶上快车道,迎来行业元年。
近日,脑科学研究院张嘉漪/颜彪团队与复旦大学集成电路与微纳电子创新学院周鹏/王水源团队、中科院上海技物所胡伟达团队合作,成功研制出了碲纳米线网络(TeNWNs)视网膜假体。这种基于材料光电特性的假体可以使失明的动物恢复可见光波段的视觉,并表现出对红外光的光感,使失明动物具备识别简单图案的能力。
在这一背景下,搜狐科技对话了杨雄里院士和张嘉漪研究员,谈谈目前国内外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现状、应用情况、挑战及风险。
刚只走了一小步,重建光明还“Long way to go”
在张嘉漪看来,脑机接口领域在神经科学中曾是一个相对小众的方向,在研究生阶段她已参与到布朗大学的脑机接口项目。近几年因为大家对“智能”的关心,以及脑科学本身的发展,“脑机接口”才逐渐成为热词。
脑机接口技术是要建立一个人工微型系统,用于采集、调控大脑活动,实现与大脑的交互。脑机接口领域具有非常强的交叉学科特征,需要包括材料、芯片、计算科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科研人员通力合作。张嘉漪与周鹏在六七年前相就认识。视网膜的感光细胞既可以等同于具有光电转换特性的半导体器件,又是整个视觉过程的导火索。这就促成他们两个团队的通力合作,研究成果展示出良好的前景。
碲纳米线具有与感光细胞相似的光反应(在实验过程中发现这种材料对近红外光也有响应)。他们合作的出发点是,当生命体失去感光能力时,如何使用这种人工材料来替代视网膜的感光细胞?
“但大脑到底感知到了哪些目前在光谱上可以区分的信号,从脑科学角度看还是不太明确,因为我们不能跟实验动物直接对话。”
张嘉漪表示,“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领域真正面临的技术挑战和问题,以及未来的应用场景,在大脑怎样接收和处理信息方面,还有很多生物机制的解析工作要做。”
杨雄里解释道,人和动物从外界获取的信息约有70%-80%都来自视觉。光在视网膜的感光细胞上产生的电信号,就像是导火索被点燃了,只要感光细胞之后的神经环路还能传递信号,在信号到达中枢后就会产生光感。光感固然重要,但是光感恢复并不意味着恢复图像辨别能力,图像形成的基础是由于图像的不同部位存在亮度反差,如果图像的不同部分亮度都一样,即没有反差,那仍无图像可言。
视网膜的神经环路精细的组构保证了对空间反差的检测。这就是说,失明者图像分辨能力是否能恢复,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视网膜外层和内层细胞的正常功能。而光感受器在病理情况下的凋亡可能导致视网膜神经环路的改变,损伤越严重,恢复就越困难。
“通过光电材料将光信号转化为电信号,这只是重要的第一步,信号如何传递至中枢,产生图像的感知,还存在很大的挑战。”杨雄里补充道。
从视网膜到中枢信号的传递过程极为复杂,在向中枢传递的不同阶段还有不同的信息处理方式,最终才形成有意义的图像。
杨雄里继续说道,“对低等动物的视网膜损伤的修复原理比较简单,因为它们的神经细胞损伤后能再生,切掉鱼、青蛙的视神经后,只要把两个断端接起来,神经就能长回去,像断指再植的情况一样。然而,哺乳动物在成年后,细胞一般不能再生,这就需要采取特殊方法使细胞再生,或者像嘉漪所说的那样,通过植入的方式恢复视觉功能。”杨雄里举例道。
谈到这,想必大家最关心的一点就是什么时候开展临床实验?
但问题来了,我们怎样保证这样的人工植入物与视网膜残留的神经环路连接起来,才能使视觉功能的恢复得比较令人满意。要知道,视网膜中神经细胞的精细连接正是其有效实施功能的关键。我们需要充分利用AI技术,与现有技术紧密结合,才能实现有效的信号传递和图像处理。
对此,张嘉漪表示:“从技术本身看,目前的人工视网膜处于1.0甚至0.5的版本。从临床应用角度来看,对于完全没有光感的病人,虽然光感恢复使病人有一定程度的获益,但我们更关注病人生活质量的实质性提高,这还需要科学家和临床医生进一步的通力合作、潜心攻关。”
“除了伦理外,还有病人的期望值。一开始病人只想重见光明,但之后就想看得更清楚,即拥有精细的图像视觉。如果只是期待看清障碍物,那还是可能企及的目标,但倘若要看得更细一些,我认为there is Long way to go。”杨雄里补充道。
把解码大脑的拼图拼起来
张嘉漪认为,视觉假体的概念听起来比较新颖,但其实牛顿就尝试过给眼睛施以机械刺激,从而得到光的感知。如何利用现有技术,向图像视觉方向上推进,是眼下最需要做的事情。
杨雄里也分享了他的看法:“脑机接口为我们认识脑活动打开了新的窗户,AI的快速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方式,但脑和机器的组构是完全不一样的,信号传递方式也不同,如何把两者结合得很完美是一个大挑战。”
“马斯克是很勇敢、很大胆的。他的基本观点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在某一天将会从整体上超过人类智能,从而危及人类社会。人类唯有借助与脑机结合成为“超人”,才能与人工智能一分高下。在这种观点的支配下,他就可能不顾一切,加大速度前进。要知道,走得太快会发生各种问题。”
既然提到了马斯克,那目前的研究与马斯克的Neuralink,以及BrainGate相比,处在怎样的国际位置?
对此,张嘉漪表示:“目前脑机接口行业在欧美工业界、学术界的公司数量不多,产业规模不是很大。我国脑机接口相关的上市公司、初创公司形成了数量上的规模,处在蓬勃发展期,但目前产业规模在生物医药行业中来看还比较有限。”
杨雄里坦言,如今AI和脑机接口技术发展迅速,中国科学家们努力在这样宏伟的态势下提出自己的观点,坚持自己的想法,是很不容易的。
当然,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也离不开脑科学基础研究的支撑。在张嘉漪看来,不管侵入式还是非侵入式,核心都是以某种方式来读取大脑活动的某种变化,再将变化和某一行为联系起来。大脑活动的变化既涉及细胞水平的群体活动,也体现在全脑范围的网络电位变化,数学、AI工具的应用在分析大脑活动的过程中必不可少。
“神经元之间递质的释放、放电方式,不同类型神经元在整个脑网络里的作用,这些问题都是目前脑科学研究所关注的。我们目前在分子、细胞、神经环路和行为学等各个层面都有一些初步的认识,但并没有完整的理论来解释什么是意识、记忆等大脑行为的生物学存在方式。等把这些问题搞清楚,就会逐步把大脑解码的拼图拼起来。”张嘉漪分享道。
“人工智能可以借鉴脑的工作原理来发展,但人工智能也会按照自己的发展态势形成一种特殊的方式,并不一定比人脑在进化过程中塑造的智能更差,人工智能已经在某些方面胜过人脑智能。”杨雄里如是说。
伦理是最大的问题
谈及未来脑机接口技术会面临哪些技术风险时,张嘉漪称,像系统的生物相容性这种工程问题是容易解决的,反倒是伦理问题更具挑战性。
在杨雄里看来,技术问题是任何一门科学发展过程中都会产生的问题,关键是在伦理上,这是最大的问题,必须把握住。
实验显示,一个人的脑电可以影响另一个人的大脑活动,即所谓的“心灵感应”。英国皇家学会的一份报告称,可以预期,在将来的某一天,人们可能通过脑电彼此交流,而毋需经语言和文字,这对提高工作效率来说有正面的意义,但如果以某种方式来控制他人脑的活动(所谓“控脑”),那很可能起负面的作用。
在神经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对心智活动的了解还刚开始,十分有限。如果把探索心智活动的奥秘比喻为对新大陆的探险,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布满新大陆周围星星点点的岛屿,真正的新大陆尚未开垦。
“未来的世界将会出现一场与我们智力相抗衡的挑战,而并不是一张舒适的软床,我们可以惬意地等候着机器人仆役的伺候。”杨雄里引用美国著名控制论专家维纳的箴言,这段对未来的预测值得我们深思!
谈及脑机接口技术在未来5 – 10年的发展情况时,张嘉漪称主要的应用场景可能还是医疗类。
“我希望未来有一到两种器械能真正地改变我们的生活,也许在未来的三到五年内,我们走在路上,会看到周围有病人植入了脑机接口设备,并真正地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张嘉漪展望道。
“在某些技术层面,可能会发展的比我们想象的还快,比如DeepSeek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就超越了我们。我可以坦率地讲,这比我预想的要快得多,例如,已经研发出现软件能快速制作一个乐曲,其巴赫风格更甚于巴赫本人的作品。”杨雄里感叹道。
不过在杨雄里看来,人工智能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比如对心智活动的规律了解地还非常肤浅。因为脑的工作机理难度极大,再加上神经系统和脑的强烈可塑性,它可以灵活变通展示出不同侧面。
谈及未来脑机接口技术发展时,张嘉漪和杨雄里都认为应该保持谨慎的态度。
很多风险在实验室里是可控的,就像张嘉漪现在做的,精细地调控视网膜神经元的活动模式、把活动模式和生成式AI的算法联系起来,完全由AI生成的图像来控制动物的神经元活动。
“通过脑机接口或视觉假体,可能向我们的大脑视觉系统输入和我们所处的世界相左的信息。所以我们必须非常谨慎,规避可能存在的伦理风险。”张嘉漪如是说。
而杨雄里更是用了“审慎的乐观”这样的表述,“我们既要乐观,也要看到问题的复杂性,如果我们不理性地用通俗的语言向普通民众解释科学的真谛和我们面临问题的复杂性,从而使他们对未来产生太高的期望值,那么到头来失望的还是民众。”
“这在科学史上是有经验的,比如有关高位截瘫者的中枢神经系统再生的问题,几十年前就有人称在几年内可以突破,使病人活动正常如初。可是尽管有所进展,但迄今为这个难题止依然困扰着我们。”杨雄里举例道。
对话最后,张嘉漪和杨雄里还谈到了我们应该如何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
张嘉漪表示:“美国在研究经费方面的投入有较大幅度的削减,这可能意味着很多华裔、非华裔的科学家在未来几年都会从美国离开,去往欧洲、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等。”
“这样一种较大规模的科学家流动可能会改变国家之间的科研实力现状,国内很多机构也都在积极张开怀抱欢迎这些出色的、在海外有很多学术成就的学者回国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张嘉漪如是说。
杨雄里则认为,未来的发展取决于“双栖”人才的培养,现在交叉领域交叉得越来越深、范围越来越广、进展越来越艰巨。一定要注重“两栖”人才的培养,而且要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开始。
“我们对年轻人这方面的培养要尽早提到日程上了,从人工智能以及脑机接口结合的发展来看,这并非是早做准备,而是刻不容缓,亡羊补牢。”杨雄里坦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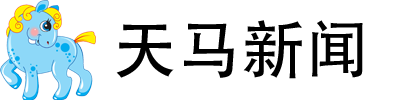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